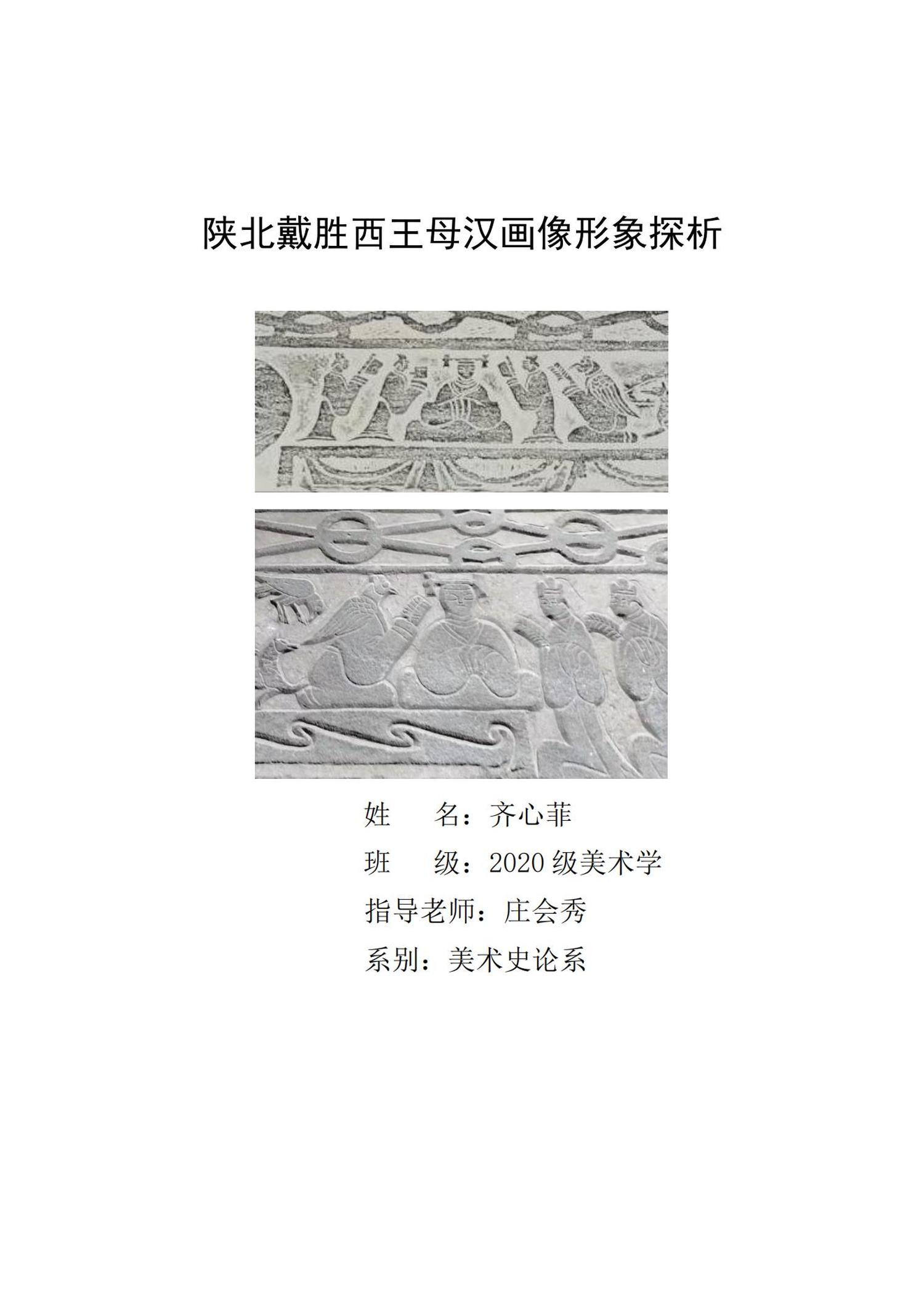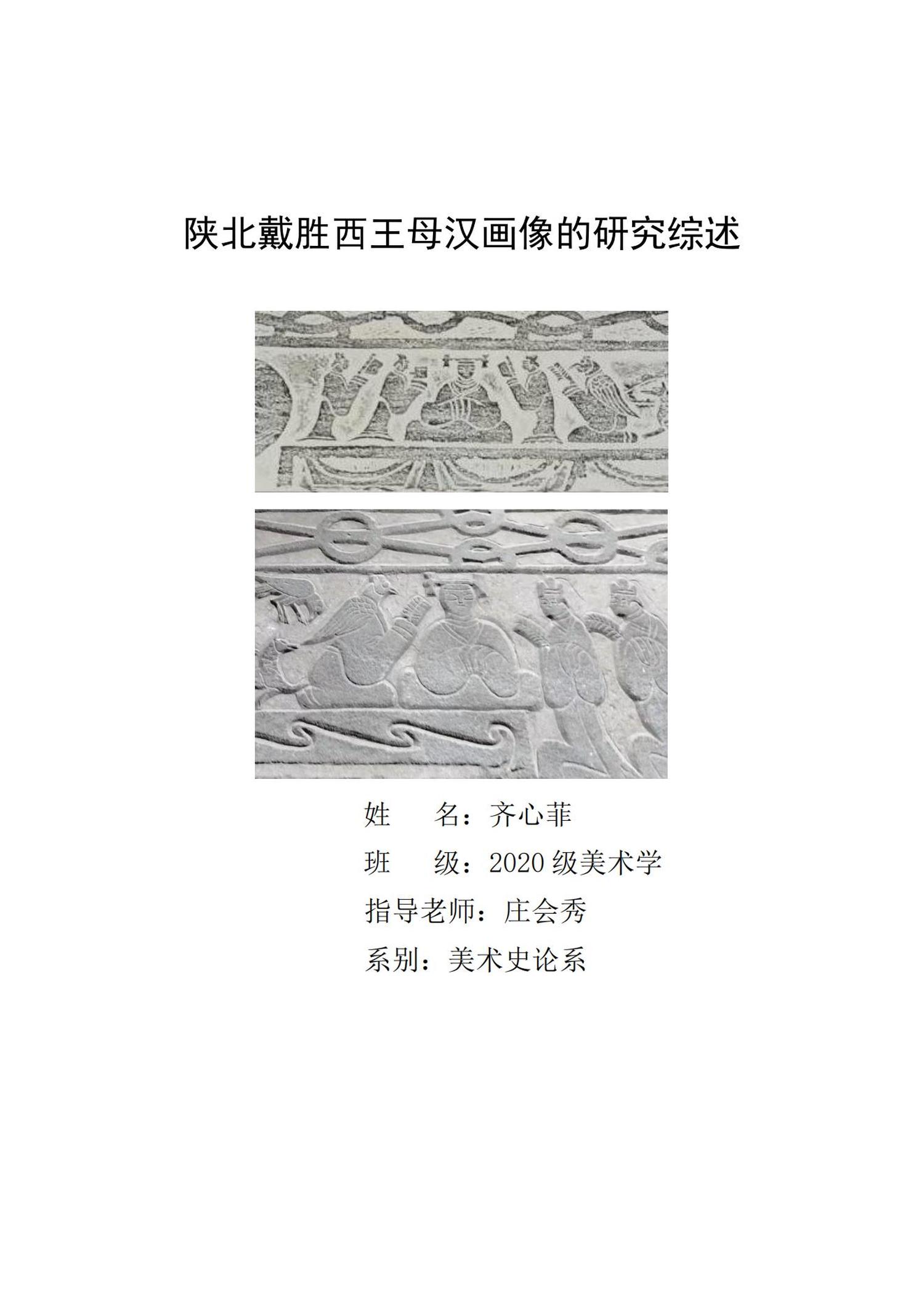陕北戴胜西王母汉画像的研究综述
最早对于汉代画像石的记载可见于东晋戴延之的《西征记》,此后虽有记述,但并非为学术意义上的研究,直到北宋中期后期“证经补史”的金石学兴起。清代金石学在结束了元明时衰微的状态后走向了复兴。19世纪末随着现代考古学的诞生和兴起,国外学者将目光转移到国内散存的汉画像石上,随即,国内学者们也纷纷加入研究汉画像石的行列中。建国以来,学术界对汉画像的研究更加科学和深入。而对于汉画像门类中最重要的母题之一西王母汉画像石的研究,则在近三十年来(1989-2020)达到新的重要阶段。
据郑州大学人文学院的谢伟对1989-2020年来对汉画像西王母图像研究的归 纳,可分为六类:一,根据图像构图内容、方式进行分类的研究(李锦山、曾琳、顾森的三分法,黄雅峰、姜生、方艳、李浥的四分法等等); 二,西王母形象与艺术表现形式的发展演变研究(李凇根据东汉永元年间和永和年间的图像差异,将其分别定义为永元模式和永和模式。[1]郑先兴提出西王母形象发展经过了“长寿之偶像”“神的救赎 ”“神的创世”三个阶段[2]。包兆会从图像学、文献学研究先秦两汉的西王母形象流变[3]。刘婵[4]、尹钊[5]等认为西王母形象经历了由原始到完善,由简到繁的过程。贾雪枫认为西王母形象经历了巫到神的嬗变[6]);三,考古辨伪研究(西王母汉画像是否出自汉代和西王母图像是否是西王母,研究的具体学者有黄明兰[7]、雷鸣夏[8]、刘辉[9]、石红艳、牛天伟[10]等); 四, 附属物研究(对附属物的整体或单一附属物的研究,研究学者有王苏琦[11]、仝涛、邹芙、郑先兴等); 五,和其他神话人物的比较研究(西王母与伏羲女娲、西王母与西方神话人物,研究学者有汪小洋[12]、陈金文[13]、高继习[14]等); 六,其他研究(研究方面有美学、民俗文化等,研究学者有朱存明、朱婷[15],郑先兴、黄诗棨、孟青等)。[16]
就目前来看,国内外学者关于戴胜西王母的形象研究的著述并不多见。巫鸿在《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中专论西王母及其图式来源,创造性地将戴胜图像、西王母图像系统和印度佛像艺术联系在一起。美国学者简·詹姆斯则在巫鸿之后对其提出的印度佛教艺术影响西王母像提出了质疑。[17]韩国全虎兑在 1997 年发表的论文中将西王母图像分为三个类型:玉胜形、非玉胜形和羽人形,以各地区的汉画像石来研究。[18]至于当前,西王母图像专题研究的唯一且较为深入的论著是李凇先生 2000 年出版的《论汉代艺术中的西王母图像》,他从图像学入手,按地域和种类分别探讨全国各地遗存中存在较有争议的西王母图像,并从考古学角度出发,对不同时期的西王母图像作了综合性的深入研究。他通过多方面考证,将有关于西王母戴胜图像及流变细致分类,并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李凇先生认为,“胜”与西王母的关系分为两个阶段:一是西汉到东汉中期,绝大多数的西王母图像都伴随有胜的出现;二是东汉后期,西王母常不戴胜,胜作为抽象符号单独出现。[19]
关于“胜”的研究,学术界主要持有两种观点,即头饰说和织胜说。头饰说即玉胜说,是对胜作为一种装饰的说法,在晋代已有:郭璞为《山海经》的《西山经》篇注“蓬发戴胜”时,言:“蓬头乱发;胜,玉胜也。”清代学者郝懿行笺疏:“郭云‘玉 胜’者,盖以玉为华胜也。”[20]织胜说有日本学者小南一郎在郭宝钧先生对古代织机的研究[21]基础上认为,将胜与织机中用来卷经线的横轴上的“勝”相联结,并提出功能说,并认为胜纹的“织”带有一种织出宇宙秩序的宇宙论的性质[22](但是他对于胜的原始意义的描述被李凇先生认为有些牵强,并且质疑了他引用六朝小说为依据的科学性。[23])此外,叶舒宪先生和王孖先生也持有功能说的观点。
除了主流观点的玉胜说和织胜说的观点,还有萧兵、郑先兴、[韩]郑在书的 “模仿说”[24](对西王母原型可能来源于上古时期某位原始部落的首领,认为“胜” 可能象征某种动物或某种动物所代表的力量),王孝廉[25]、韩高年[26]的“神职说” (有学者从《山海经》中对于西王母“司天之力而掌五残”的神职描述,认为胜是西王母神职的象征),鲁维一的“神王说”(认为胜是西王母形象的神性特征,此外还将胜看做王权的象征。),陆思古的“神权说”,[韩]全虎兑的“阴阳说”,生殖崇拜说等等。王薪在《从汉墓考察西王母“戴胜”图像涵义及流变》中把已有的这些观点总结为六类:华胜说,功能说,图腾象征说,神职说,阴阳说、生殖崇拜说以及神王说。[27]
注释
[1] 李淞:《从永元模式到永和模式: 陕北汉画像石中的西王母图像分期研究》,《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5期,第56-67页。
[2] 郑先兴:《汉画中的西王母神话与西王母崇拜》,《古代文明》,2008年第5期,第97-114页。
[3] 包兆会:《山海经与汉画像中的西王母形象变异》,《美术研究》2013年第5期,第30-38页。
[4] 刘婵:《汉代考古遗存所见西王母形象及其反映的思想内涵》,《文学界》2010年第5期,第184页。
[5] 尹钊、刁海军、侍银银等:《汉画像石上西王母形象的演变》,《东方收藏》2010年第9期,第29-30页。
[6] 贾雪枫:《汉画像石中西王母的形象及其嬗变》,《文史杂志》2014年第4期,第49-51页。
[7] 黄明兰:《穆天子见西王母汉画像石考释》,《中原文物》1982年第1期。
[8] 雷鸣夏:《“穆天子会见西王母”画像石质疑》,《中原文物》1983年第5期。
[9] 刘辉:《沛县栖山石椁墓中的“西王母”画像管见》,《四川文物》2010年第1期。
[10] 石红艳、牛天伟:《关于西王母与女墓主形象的辨识问题: 与刘辉商榷》,《四川文物》2011年第5期,第55-60页。
[11] 王苏琦:《四川汉代“龙虎座”西王母图像初步研究》,《四川文物》2005年第2期,第62页。
[12] 汪小洋:《汉壁画墓中西王母、女娲图像的辨析与意义》,《艺苑》2008年第1期,第4-12页。
[13] 陈金文:《东汉画像石中西王母与伏羲、女娲共同构图的解读》,《青海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第125-128页。
[14] 高继习:《白色的西王母: 西王母与雅典娜神话的比较研究》,《西部考古》2017年第4期,第145-177页。
[15] 朱存明、朱婷:《汉画像西王母的图文互释研究》,《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第86-91页。
[16] 谢伟:《汉画像西王母图像近三十年研究综述》,《平顶山学院学报》2021年第8期,第4期。
[17] [美]简·詹姆斯:《汉代西王母的图像志研究》,1997年第2期。
[18] [韩]全虎兑:《汉代画像石中的西王母》,《美术资料》第59号,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1997年。
[19] 李凇:《论汉代艺术中的西王母图像》,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49页。
[20] 郝懿行,栾保群:《山海经笺疏》,中华书局2019年11月。
[21] 郭宝钧:《古玉新诠》,《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本下册 ),商务印书馆1949年。
[22] 小南一郎著:《西王母与七夕文化传说》,1974年。
[23] 李凇:《论汉代艺术中的西王母图像》,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51页。
[24] 叶舒宪、萧兵、[韩]郑在书:《山海经的文化寻踪——想象地理学与东西方文化的碰撞》,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25] 王孝廉:《西王母与周穆王》,《中国神话与传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汉学研究中心1996年版。
[26] 韩高年:《<山海经>西王母之神相、族属及其他 》,《西北民族研究》2013年2月。
[27] 王薪:《从汉墓考察西王母“戴胜”图像涵义及流变》,《西部学刊》2018年第6期。
陕北汉画像戴胜西王母形象探析
西王母是研究汉画像石的最重要母题之一,而胜又是陕北西王母汉画像中常见的元素,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在此笔者将会在后面探讨陕北戴胜西王母的形象。
一、文献中的西王母形象
(一)先秦文献中的西王母形象
李凇先生认为,关于西王母的记载,最真实可信的资料出自战国时期。[1]庄子(约公元前369—公元前286)在《庄子·大宗师第六》提到各位神祇和上古帝王得“道”后的结果,其中提到“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广,莫知其始,莫知其终”,是以长生。但坐拥昆仑山的是堪坏(胚),而“坐乎少广”的西王母。[2]同为战国时期的《山海经》(现代多数学者认为,《山海经》可能为多人所著,约为战国初年至西汉初年楚和巴蜀地区的人所作至西汉刘歆校书时才将其合编到一起。),有四处描写涉及西王母:
1.又西北三百五十里,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 西山经 第二》)[3]
2.“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日昆仑之丘。……有人戴胜,虎齿,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大荒西经 第十六》) [4]
3.西王母梯几而戴胜(杖)。其南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在昆仑虚北。(《海内北经 第十二》)[5]
4.(西有)〔有西〕王母之山、壑山、海山。……有三青鸟,赤首黑目,一名曰大鵹,ー名少鵹,一名曰青鸟。(《大荒西经第十六》)(此段原为 “西有王母之山”, 据王念孙、郝懿行校改为“有西王母山”)[6]
其中,第1、2、3段是对西王母的直接描写,但仔细探究就会发现一个问题,显然这三段中对于西王母的形象描写不尽相同,但又同时指出西王母有“戴胜”的形象特点。尽管西王母身上佩戴了“胜”这一出于某种目的的“饰物”,但同样的,西王母身上带有浓厚的原始蛮荒特征。正如费尔巴哈所说,“动物是人不可缺少的必要的东西,人之所以为人,要依靠动物,而人的生命和存在所依靠的东西,对人来说就是神”。[7]原始先民对无法掌控自己生命的自然加以敬畏与崇拜,于信仰方面创造了各种以兽类为原型的保护神,寄希望于保护神能拥有动物的能力以庇佑自身。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早先的西王母这样的神灵形象会被描绘成半人半兽的状态,相应地,祂拥有司掌瘟疫灾病、主宰刑罚的能力。虽然有很多学者对此时的西王母持有“凶神说”的看法,但其蛮荒原始的状态是毋庸置疑的。
此外,第1段“西王母其状如人”、第2段“有人戴胜,虎齿,豹尾,穴处”与第3段“梯几而戴胜(杖)”相比较,可看出对西王母的描述正经历人化的演变,即体现了“人”自我意识、自我认知的萌发状态,于是可以判断这三段的描述应出自不同时段。(日本学者小南一郎认为,第 1 段属最古老的层次,可推定为上溯至战国初期的观念。[8])
《穆天子传》中也有对西王母的记载,它是在晋武帝咸宁五年(公元279年)在汲郡出土的,后藏于秘府[9],由晋武帝司马炎派荀勖等人参与整理,现今只《穆天子传》存世。《穆天子传》共6卷,其中前5卷记载周穆王西征昆仑并与西王母相会的故事,虽然其中周穆王西征的历史事件与西王母相会的神话事件杂糅,但是确为可供研究西王母的史料。(上世纪末已有学者分别肯定了这份史料的研究价值。)
其中对西王母的描述如下:
癸亥,至于王母之邦。吉日甲子,天子宾于西王母。乃执白圭玄璧,以见西王母。好献锦组百纯,□组三百纯。西王母再拜受之。□乙丑,天子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天子谣曰:“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天子答之曰:“予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汝。比及三年,将复而野。”
西王母又为天子吟,曰:“徂彼西土,爰居其野。虎豹为群,於鹊与处。嘉命不迁,我为帝女。彼何世民,又将去子。吹笙鼓簧,中心翔翔。世民之子,唯天之望。”天子遂驱升于弇山。乃纪名迹于弇山之石,而树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
从这两段的记述中可以看出,西王母的形象,已从《山海经》中的“蓬发戴胜”“豹尾虎齿”且“善啸”的原始蛮荒状态,转变成一位已经脱离兽形的特征仍带有一点原始性质(“虎豹为群,於鹊与处”),但明显能与天子从容同游同吟的文明化了的女子,同时,也不难看出,此时的西王母似乎已拥有予人长生的神通,而非单纯只是传播灾难和疫病、司掌五刑残杀的凶神了。
(二)两汉文献中的西王母形象
1.西汉文献
(1)成书于西汉初期的《淮南子》,有三处提及西王母:
1.卷四《地形训》:“西王母在流沙之濒。”[10]
2.卷六《览冥训》:“逮至夏桀之时,主暗晦而不明,道澜漫而不修;……西姥折胜,黄神啸吟……”(西姥即西王母)[11]
3.卷六《览冥训》:“譬若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怅然有丧,无以续之。”[12]
这3段文献中,只有第2段为关于西王母戴胜的记载,言夏朝末年时期,桀作为帝王却残暴昏庸,天下混乱,西王母折断头上所戴之胜。这份史料直接描述了戴胜的西王母形象。
太史公始于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著《史记》,前后经历了14年,此段时间大致为西汉中期。书中有三处提及西王母,而确切提到有关于西王母形象记载的却是七十《列传》中《司马相如传》中引用司马相如的《大人赋》:
“西望昆仑之轧沕洸忽兮,直径驰乎三危。排阊阖而入帝宫兮,载玉女而与之归。舒阆风而摇集兮,亢鸟腾而一止。低回阴山翔以纡曲兮,吾乃今目睹西王母皬然白首。戴胜而穴处兮,亦幸有三足乌为之使。必长生若此而不死兮,虽济万世不足以喜。”[13](后录入《汉书》略有异:“吾乃今日覩西王母暠然白首”。[14])
从司马相如的《大人赋》中可以看出,他所认为“皬(暠)然白首”、“戴胜穴处”是西王母的形象特征,或许是当时汉代人对西王母形象认知的普遍“标准”的映射。
西汉末年的杨雄(公元前53年—公元18年)崇拜司马相如,在随从成帝(在位公元前33-公元前7年)出游甘泉宫时,也作了一首与司马相如《大人赋》相似的宏伟华丽篇章《甘泉赋》,更相似的是他在赋中也联想到西王母:“风傱而扶辖兮,鸳凤纷其御蕤。梁弱水之潇漾兮,蹑不周之逶蛇。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寿兮,屏玉女而却虙妃。玉女无所眺其清卢兮,虙妃曾不得施其蛾眉。”[15]从中可以看出西王母身边有两位美丽的神女——玉女和虙妃相伴,代替了司马相如笔下的“三足乌”,亦非其它非人神兽。这也从侧面上反映出对于西王母的想象,已经完全合乎世人具有较高程度的“文明化”的审美了。
2.东汉文献
东汉的文人在作品中描述西王母时,显然是带有一定的浪漫色彩的情调在其中的。例如张衡也以同样浪漫而华贵的笔调想象西王母:“聘王母于银台兮,羞玉芝以疗饥。戴胜愸其既欢兮,又诮余之行迟。载太华之玉女兮,召洛浦之宓妃。咸姣丽以蠱媚兮,增嫮眼而蛾眉。”[16]
与上层文人的视角不同,民间的西王母扮演的更多是被信仰的“救世主”神灵角色。西汉末年汉哀帝在位期间,基于对连年的大旱的持续悲观的态度,民间在哀帝建平四年(公元前3年)爆发了大规模的恐慌,民众为了生存,争相聚集在一起对西王母进行祭祀运动。班固在《汉书》卷二十七的《五行志》中详细记载了这件事:“哀帝建平四年正月,民惊走,持藥或橄一枚,传相付与,曰行诏筹。道中相过逢多至千数,或被发徒践,或夜折关,或逾墙入,或乘车骑奔驰,以置驿传行,经历郡国二十六,至京师。其夏,京师郡国民聚会里巷阡陌,设祭张博具,歌舞祠西王母。又传书曰:‘母告百姓,佩此书者不死。不信我言,视门枢下,当有白发。’至秋止。”[17]
(另,班固在《汉书》中的《哀帝纪》和《天文志》中也有相关记载,但不及《五行志》中的详细,固不再引用文献赘述。)这场发起自民间、从地方郡国传至京师的、时长达大半年的西王母祭祀崇拜活动,被李凇先生认为是“民众在社会危机中向西王母伸出求援之手(而不是向官方祭祀的神灵如五帝、太一、后土),说明了西王母信仰的性质转换,即实际上已由神话走向了宗教崇拜”。[18]鲁惟一先生和巫鸿先生先后指出了其中中有组织的宗教因素:象征物(诏筹、博具),祭仪,升火,崇拜的偶像,有组织的活动等。显然,此时地方上至京师的民间对于西王母的崇拜,已经上升到较为系统的体系——即宗教意义上的崇拜。
(三)与东王公“配对”的西王母
西王母作为汉代民间信仰的神灵已久,但在早先一直处于一种“独尊”的状态,后来出现了东王公作为与西王母相配对的男神出现。虽然在东汉文献中难以找到确凿的文字,但他的名字却多次出现在东汉中期的铜镜铭文中。已知最早明确提到东王公并制作年份详细的铜镜是藏于日本五岛美术馆的“元兴元年环状乳神兽镜”,有铭文“元兴元年(公元105年)五月丙午日天大赦,广汉造作尚方明竟,幽涑三商周得无极,世得光明长乐未英,富且昌宜侯王,师命长生如石,位至三公,寿如东王父、西王母,仙人子立至公侯”。[19]据此可知,东王公形象“诞生”的最晚下线是东汉的中晚期。
《神异经》记录了东汉时期西王母与东王公相配对的形象:“昆仑之山有铜柱焉,其高入天,所谓天柱也。围三千里,圆如削,下有回屋,方百丈,仙人九府治之。上有大鸟,名曰希有,南向,张左翼覆东王公,右翼覆西王母。背上小处无羽,一万九千里。西王母岁登其上,之东王公也……阴阳相通,惟会益工。” [20]
依托于文献记载和前人的研究成果,比较战国时期与两汉时期的文献(考虑到部分文献比较有争议,如六朝人伪托班固所撰的《汉武帝内传》和《汉武帝故事》等,故不多引用在此处分析),可以推测出西王母于历史文献中的形象的衍变,可得到一条比较清晰的发展脉络。
①形象上:从半人半兽的蛮荒原始状态,逐渐发展为文明化、理想化的美貌女神形象;
②地位上:由一开始的个人“独尊”,到身边出现侍从,再到与东王公的配对形成一种均衡的形式。
③性质上:从单纯传播灾难和疫病、司掌五刑残杀的凶神,到掌握长生不死神通的神灵,再到保佑生灵、赐福避灾的神明。
二、胜的形象
李凇先生认为,西王母汉画像石中的核心图像是西王母(戴胜)和玉兔。[21]在汉画像石中,“胜”常常作为西王母重要的形象特征出现,甚至有部分画像以“胜” 作为西王母的标志。因此在研究戴胜西王母的形象及其内涵时,研究的视线会不可避免地提到西王母所戴“胜”的种种问题,由于研究的重点不在于“胜”的本身,笔者对此部分只做简要分析。有关西王母所戴的胜,学术界主要持有两种观点,即头饰说和织胜说。
头饰说源于晋代郭璞为《山海经》的《西山经》篇注“蓬发戴胜”时,言:“蓬头乱发;胜,玉胜也。”(清代学者郝懿行笺疏:“郭云‘玉胜’者,盖以玉为华胜也。”)[22]颜师古在为前文所提到的司马相如《大人赋》“戴胜而穴处”注释:“胜,妇人首饰也,汉代谓之‘华胜’。”[23]
织胜说即把“胜”看作是织机上用来卷经线的横轴上的“滕”。《淮南子·汜论训》:“伯余之初作衣也……后世为之相杼胜复,而民得以揜形御寒。”段玉裁注:“胜者,滕之假借字。”[24]日本学者小南一郎在郭宝钧先生对古代织机的研究[25]基础上,把胜与汉画像中的纺织图加以对照,得出滕是胜的原型的结论,并认为西王母与纺织有着密切联系,推测“织”具有宇宙论的性质特点。[26]此外,叶舒宪先生和王孖先生也持有织胜装饰物的观点。
除了主流观点的玉胜说和织胜说,还有萧兵、郑先兴的“模仿说”[27],王孝廉[28]、韩高年[29]的“神职说”,鲁维一的“神王说”,陆思古的“神权说”,(韩)全虎兑的“阴阳说”等等。
此外,胜还作为一种祥瑞符号,即抽象成一种象征性的符号。山东嘉祥武梁祠屋顶后有一处关于玉胜的图像,图中的玉胜像两枚糖果的简笔画,用一根竖条连接在一起,旁边有榜题“玉胜王者”(见图1,采自王薪:《从汉墓考察西王母“戴胜”图像涵义及流变》,《西部学刊》2018年第6期)。唐《开元占经》引《晋中兴书·征祥说》:“金胜者,仁宝也。不琢自成,光若水月,四夷宾服则出。”又有《宋书·符瑞志》载:“金胜,国平盗贼,四夷宾服则出。晋穆帝永和元年二月,舂谷民得金胜一杖,长五寸,状如织胜。”不仅道出了胜的祥瑞含义,同时也为织胜说提供了例证。[30]

图1
三、陕北地区图像中的戴胜西王母形象
李凇先生认为,“胜”与西王母的关系分为两个阶段:一是西汉到东汉中期,绝大多数的西王母图像都伴随有胜的出现;二是东汉后期,西王母常不戴胜,胜作为抽象符号单独出现,“开始流行不戴胜的高髻或戴巾帼像”,“皇室和贵族亦佩戴胜,胜的涵义向两方面转化:实用和祥瑞物”。[31]
陕北地区的汉画像石种类丰富,其中西王母画像石的数量占据大半。近半个世纪以来,陕北地区发掘的汉画像石多达700多块,仅绥德县就出土了570多块。[32]因此在讨论陕北地区的汉画像石时,可以以绥德地区的汉画像石作为代表。
关于收集到的绥德地区的戴胜西王母形象,代表有如下:


(二)图像探析
观察上面的图例,绥德的汉画像西王母常见的头饰图像有以下几种,戴胜、戴冠和不戴。
戴胜图像(02、04、06、08、09、11、12)的胜,以上文例证祥瑞符号胜所引用的图1为主要形状作不同的变体。在出土的实物中,与之对应的有朝鲜乐浪古坟发掘出的玉胜[33](图2[34]),江苏邗江甘泉2号东汉初期墓中出土的三件金胜[35](图3[36])等。其中08、09号为同一种样式,西王母所佩戴的胜的样式最接近于该类玉胜,且皆位于横额最左或最右等显眼位置。此外,西王母正面画像石外,左右两边簇拥着侧身手持便面的侍者,此外还配有捣药玉兔、九尾狐和青鸟等西王母神话体系中常见的神兽。(以图4为例)


图2 图3

图4 四十铺镇田舫墓横额
戴冠图像有01、05、07。其中,01西王母所戴冠为三个角朝上的尖冠,较东王公所戴的冠略显精致小巧;05西王母头上所戴的发饰形象较为模糊,与右侧东王公所戴的冠相差无异,故把其归为戴冠形象;07西王母与东王公所戴冠四四方方,二神在全身形象上相差无异。西王母戴冠形象多为东汉中后期,有学者认为西王母戴冠是道家为自家最高地位女仙美化的结果,在美化的过程中反倒把西王母原本戴胜的形象特点给遗忘了,更遑论祂早先“蓬发戴胜”的形象。[37]
不戴胜(冠)西王母又有10无胜(冠)西王母和03牛头西王母。10西王母梳髻下垂,与戴尖冠的东王公对比明显。03西王母以牛首人形象出现,对应的东王公以鸡首人的形象,可以说,这样的西王母和东王公是后人对神话的改造的变异产物。有学者认为,鸡首人身和牛首人身成为社会下层的信仰崇拜成对出现于陕北汉画像石中,一是由于这两种动物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二是汉人对阴阳五行学说的信仰。总之,这种创新性的神祇实际上是民众对生活中某种需求渴望的产物。[38]
除上述绥德地区的西王母形象,还有神木大保当M24墓出土的戴冕西王母(图5[39]),位于墓门左立柱画像石。其发掘报告载:“画面主题刻西王母像。西王母戴冕冠袖手盘坐于悬圃顶端斗栱形座上,冕冠前后各垂四旒。《释名·释首饰》:‘冕犹俛也挽,挽平直貌也;亦言文也。玄上纁下,前后垂珠,有文饰也’。先秦冕制见于《周礼·司服》,只有高级贵族才戴它。西汉时,冕或已废置不用,东汉明帝改定服制时援古说而制冕,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画像石中出现过冕,但没有垂饰,大保当 M24门柱西王母所戴的这顶冕冠,是目前所见最接近文献描述形状的画像石作品。另外,西王母戴冕的形象也极为罕见。”[40]

图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