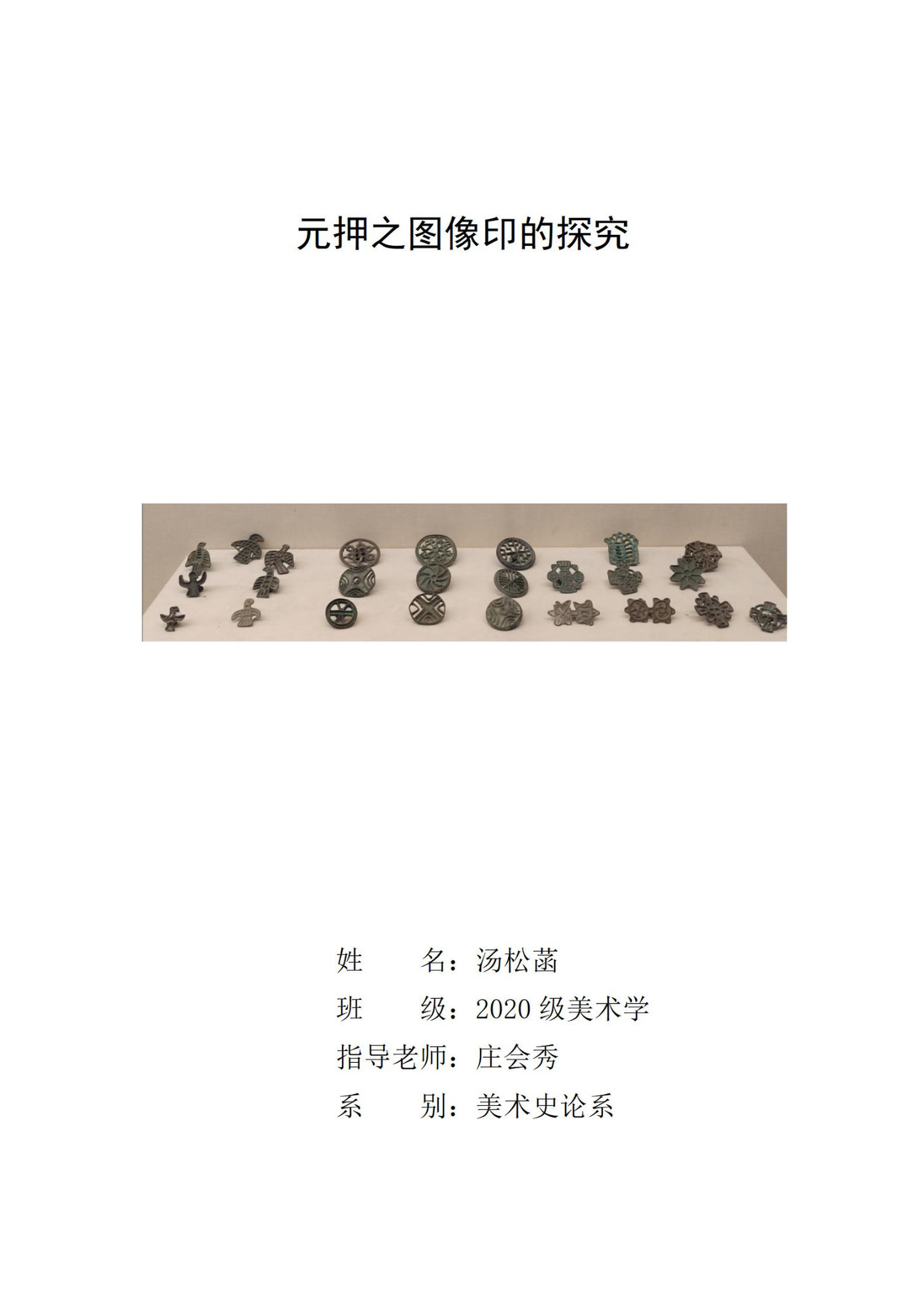元押之图像印的探究
2020级美术学 汤松菡
一、有关花押印的早期记载和研究
明代郎瑛的《七修类稿》[1]有记载:“古人花押所以代名,故以名字而花之。”这是对花押初步、简练的见解,清人陈炼在《印说》[2]中有言:“印虽必遵秦汉,然元明诸公之印之佳者,亦可为法。”秦汉印固然是篆刻经典,但元代佳印仍可为现世效法。清人陈澧的《摹印述》[3]:“赵松雪始以小篆作朱文印,文衡山父子效之,所谓圆朱文也,虽非古法,然自是雅制。”清人谈迁在《北游录》[4]中记载了蒙古帝王制花押印一事:“甲午二月六日,上召陈名夏作一押字,便于制书。”而清人杨守敬的《元押》[5]、《印林》[6],则对于元押印在后世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元押》一书中所收藏的四百余枚印蜕以单字元押为主,生肖花押、吉语印等少量混入其中,《印林》则含千余枚印蜕,这两本书籍是早期为数不多的元押专辑,此外还有殷尘的《邦斋宋元押印存》[7]等。
然而奇怪的是,自清灭亡后的几百年间,有关元押印的研究少之又少,直至近代才有所增多,但相比其他朝代的研究,元押似乎并不受到认可。翻阅近代中国大部分印章史类书籍可以发现,多数书籍的作者在梳理探究印章史时会人为地跳过元代,或者只是简单地概述一番,更不用提对元押的细致探究了。少数印章史书会有较多笔墨去撰写,但也主要探讨元代汉印,而非因时代变迁注入新鲜血液的元花押印,黄淳在其书《中国古代印论史》[8]中提到了元人赵孟頫与吾衍对于复兴汉印的成就和意义以及在其影响下的元代文人的印章审美观,但并没有提及当时具有改革和创造意义的元押在印论史中的影响等,只是针对元代这一时期下文人对早代印章的延续进行探究,但这也无可厚非,此书开创性的创举以及其内在的内涵与逻辑值得我们去学习,萧高洪的《篆刻史话》[9]亦以元代文人与汉印的传承为主题进行研究,并无涉及元押。有两本印章史书对元押印有较为细致的探究:刘江的《中国印章艺术史》[10]与赵昌智、祝竹的《中国篆刻史》[11],包括元押印的起源、地位、类型、特征、印材发展、印章应用、艺术价值及影响,对初步了解元押印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探究印界对元押的评判之态,可从多方考虑,笔者认为,从元押印本身的文字构成上来讲,八思巴文、西夏文、女真文、白文、梵文、畏兀式蒙古文、回鹘式蒙古文以及现在仍旧未知的少数民族文字由于传世解说资料稀少而难以释读,这些纷繁复杂的多民族文字在为元押印增添光彩和研究价值的同时,其研究难度之大也使大部分学者望而退步,元押印得不到细致真实的论述,其本身也就不能被认解。从其风格特色上来看,相比于秦汉印的儒雅厚重以及宋、明、清时期印章的清丽、“艺术”,元押印更趋近于实用、“俗气”,对于现代大部分研究者来说,“宗秦法汉”的原则不可违背,实用俗气的印章也不能与风雅艺术的印章相媲美。另外,对元代历史认知的缺乏,甚至是偏见,也给现代研究戴上了一双有色眼镜,二十四史中的《元史》[12]最受争议,有诸如“古今史成之速,未有如《元史》者,而文之陋劣,亦无如《元史》者。”的言论,由于编撰过于草率,行文简陋而导致批评,这确实是因实而论,但作为史料,《元史》的价值不可低估,元代大部分史料因《元史》的记载才得以保存下来,不能以区区草率、简陋等词一概论之。对于元押的研究,也是一样的道理,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13]中有言:“今蒙古色目人之为官者,多不能执笔花押,例以象牙或木刻而印之。宰辅及近侍官至一品者得旨则用玉图书押字,非特赐不敢于。”这种说法虽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对于元人入印的缘由却也过于简单潦草,流传至今,如今的许多文章在介绍花押印时仍在完全引用此段文字。元押长期被低估,其价值不能充分展现出来,但令人感到欣慰的是,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发觉到元押的多方价值,周晓陆的《元押》[14]集元押之精华,通过琳琅满目的元押为我们重现了被蒙尘几百年的恢弘大观,《元押》之首的《押印杂谈》[15]一文亦是有关于元押的精华之作。
二、有关花押印研究的画册类和著作类书籍
随着越来越多的资料的出现以及当代学者的逐步重视,元押印的研究也得到了更深一步的发展,元押印的研究更具有针对性和普及性。
有关花押印研究的画册类书籍主要有:1994年文雅堂杨广泰君手钤我的印藏《亦无楼宋元古印辑》[16],为近数十年的元押印谱的开端。1995年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花押印汇》[17],由著名书法家、篆刻家、西冷印社社员施元亮先生所著,施元亮先生从文化背景、绘画艺术、书法艺术等多方面对所收集的作品进行了细致的分类和研究。1998年荣宝斋出版社出版的《古代玺印辑存》[18],作者选堂。2006年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王本兴著《印章章法分类》[19],从虚实、印文、点画三方面对印章进行分类和研究。2008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郑珉中、方斌著《玺印》[20]。2010年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版,顾从德著《集古印谱》[21]。2010年吉林美术出版社出版,孙慰祖著《历代玺印断代标准品图鉴》[22]。2014年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出版,马炜著《中国历代篆刻精华—历代印》[23]。2017年九州出版社出版,汪自力、王钧、孙惠民著《民间藏历代押印图录》[24],该书全面展示了近二十年来民间收藏元押印章的现实状况,共收录了1002个印拓,除图像之外,此书还爬疏了汉字、少数民族文字、花押、图像印、景教印等诸多印章的源流,并大致梳理了元押从南北朝至民国的发展路径。
有关花押印研究的著作类书籍主要有:1986年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唐耕耦、陆宏基著《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25],此书中有大量的敦煌地区出土的花押实例,对研究敦煌地区花押发展提供了可观的资料。1999年西冷印社出版社出版,沙孟海著《印学史》[26],有关花押印的内容较少。1999年重庆出版社出版,黄淳著《元代印风》[27],分析了元代文人三个阶段对印章艺术的认识,勾画出元代文人印章发展轮廓,包含了元代押印、元代文人印等的探究。1999年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孙慰祖著《孙慰祖论印文稿》[28]。2001年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唐汉钧著《唐宋元私印押记集存》[29],书中对八思巴文印记、花押印记、图形印记等都有详细研究。2002年地质出版社出版,张锡英著《中国古代玺印》[30]。2003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田建平著《元代出版史》[31],作者另辟蹊径,从印刷、出版的角度重解元押,并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领域探索元押兴起和传播的原因以及元押在社会中的影响。2006年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出版,印农著《中国印》[32],书中稍加提及元押。2009年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郭兵著《寸心籀篆—中国古代玺印鉴赏》[33],书中介绍了花押印的由来,从印台、印文、形状、寓意等多角度分析了书中附带的多张花押印图案。2010年岭南美术出版社出版,苏晨著《印章的风景》[34],有关元押的笔墨并不多。
三、元花押印针对性研究成果
集中对元押中的某一种类进行研究的书籍或论文,主要有孙家潭先生所著,2010年荣宝斋出版社出版的《元代无边栏押印与黑城文书》[35]、2003年西冷印社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印章:孙家潭作品集》[36],该作品集中收录了多篇有关元押的研究文选,如《蒙元时期独特的蒙汉文种混合印》[37]、《宋元无边栏押印钩沉》[38]、《壬午马年话马押》[39]、《宋元的飞鸟形押》[40],周伟洲《陕西出土与少数民族有关的古代印玺杂考》[41]有关元押印十字式的解读等,这些研究将神秘莫测的元押印一点点地扒开,从细微到全貌,也为后序的研究提供了资料与方法。
四、八思巴字文印研究成果
有关八思巴文印等少数民族印的研究的书籍、期刊或论文主要有:孙慰祖先生编著的《孙慰祖论印文稿》[42],在元八思巴字私印研究的章节中列举了八思巴文印与元押印图案,但由于私印的断代难度大,书中所列举的一些私印无法与当时的社会背景相联系,仍需继续探究。孙慰祖先生还在八思巴文的篆刻与研究专题的期刊中,以八思巴字印系的特征及其社会融入[43]为主题进行探究。马晓林的《碑刻所见蒙元时期全真掌教印章及相关史事研究》[44],从宗教的角度探索八思巴字印,开拓出新的研究思路。照那斯图的《步辇图》上的两颗元国书鉴藏印译释—兼谈古代书画题跋中八思巴字印[45]、《元八思巴字篆书官印辑存》[46]、《八思巴字篆体字母研究》[47]、《八思巴字与蒙古语文献I研究文集》[48]、《台湾故宫藏几方元八思巴字印译释》[49]等,作者从多方搜集八思巴字印,以自己精湛的专业知识和独特的见解不断探寻着八思巴字印背后的秘密。叶其峰的《故宫藏元八思巴字印及相关问题》[50],作者选取了多种八思巴文字印章及印文资料加以介绍,并对相关问题提出个人看法。杨永财的《八思巴文“元押”印章在杜尔伯特出土》[51]、《风从北方来—内蒙古八思巴文篆刻进京展元代八思巴文印章选》[52]以及哈斯喜贵《哈斯喜贵篆刻集》[53]、刘玉江的《哈斯喜贵篆刻艺术》[54]、于佳音的《回鹘文经济文书t(a)mya和ni(?)an研究》[55]等,对部分含有少数民族字印的元押印的识别和研究提供了一些宝贵的资料和见解。在元押印文释读方面,照那斯图的《蒙古字韵校本》[56]、孙家潭的《关于八思巴文字印释读的几点体会》[57]和《蒙元时期独特的蒙汉文种混合印》、赵芯的《姓氏押之汉字“姓”和“花字”押》[58]等,前三者对研究八思巴文印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后者则是对元押印其他种类印式的解读和阐述提供了参考。
五、元花押印国外研究成果
关于国外对元押印的研究,笔者能力有限,仅找到了法国龙乐恒所编《伯希和旧藏花押印集》[59],法国学者伯希和虽专门研究元代玺印,但文字著作却甚少,仅存两篇涉及八思巴文与景教印,一是1927年3月11日向法国亚洲研究会所做《八思巴文字母渊源考》[60]演讲,但如今尚未发表,二是1931年发表的《发现于河西的白鸽、十字刑铜质印符考》[61]。另外还有日本学者石黑ひさ子的《墨书陶瓷上的花押和宋元花押印》[62]、久米雅雄的《日本花押与中国大名印章》[63]。
注释
[1](明)郎瑛:《七修类稿》卷二十五辩证。
[2](清)陈炼:《印说》第十六段。
[3](清)陈澧:《摹印述》,《美术丛书》本。
[4](清)谈迁:《北游录》•北游录纪闻下之【押字】。
[5](清)杨守敬:《元押》,1877年编,现收录于《杨守敬集》湖北人民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6](清)杨守敬:《印林》,现收录于《杨守敬集》湖北人民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7](清)殷尘:《邦斋宋元押印存》(二卷)。
[8]黄淳:《中国古代印论史》,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年版。
[9]萧高洪:《篆刻史话》,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10]刘江:《中国印章艺术史》,西冷印社出版社2005年版。
[11]赵昌智、祝竹:《中国篆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12]《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版。
[13](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
[14]周晓陆:《元押:中国古代篆刻艺术奇葩》,江苏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
[15]周晓陆:《押印杂谈》,《元押:中国古代篆刻艺术奇葩》首页,江苏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
[16]文雅堂杨广泰君手钤我:《亦无楼宋元古印辑》。
[17]施元亮:《花押印汇》,上海书画出版社1995年版。
[18]选堂:《古代玺印辑存》,荣宝斋出版社1998年版。
[19]王本兴:《印章章法分类》,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版。
[20]郑珉中、方斌:《玺印》,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版。
[21]顾从德:《集古印谱》,吉林出版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版。
[22]孙慰祖:《历代玺印断代标准品图鉴》,吉林美术出版社2010年版。
[23]马炜:《中国历代篆刻精华—历代印》,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2014年版。
[24]汪自力、王钧、孙惠民:《民间藏历代押印图录》,九州出版社2017年版。
[25]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
[26]沙孟海:《印学史》,西冷印社出版社1999年版。
[27]黄淳:《元代印风》,重庆出版社1999年版。
[28]孙慰祖:《孙慰祖论印文稿》,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
[29]唐汉钧:《唐宋元私印押记集存》,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
[30]张锡英:《中国古代玺印》,地质出版社2002年版。
[31]田建平:《元代出版史》,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32]印农:《中国印》,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
[33]郭兵:《寸心籀篆—中国古代玺印鉴赏》,湖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
[34]苏晨:《印章的风景》,岭南美术出版社2010年版。
[35]孙家潭:《元代无比栏押印与黑城文书》,荣宝斋出版社2010年版。
[36]孙家潭:《中国印章:孙家潭作品集》,西冷印社出版社2003年版。
[37]孙家潭:收录于《中国印章:孙家潭作品集》,西冷印社出版社2003年版。
[38]孙家潭:收录于《中国印章:孙家潭作品集》,西冷印社出版社2003年版。
[39]孙家潭:收录于《中国印章:孙家潭作品集》,西冷印社出版社2003年版。
[40]孙家潭:收录于《中国印章:孙家潭作品集》,西冷印社出版社2003年版。
[41]周伟洲:《陕西出土与少数民族有关的古代印玺杂考》,《民族研究》2000年第2期。
[42]孙慰祖:《孙慰祖论印文稿》,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
[43]孙慰祖:《八思巴字印系的特征及其社会融入》,《中国书法》2018年。
[44]马晓林:《碑刻所见蒙元时期全真掌教印章及相关史事研究》,《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45]照那斯图:《步辇图》上的两颗元国书鉴藏印译释—兼谈古代书画题跋中八思巴字印,《故宫博物院院刊》1999年第1期。
[46]照那斯图:《元八思巴字篆书官印辑存》,《文物资料丛刊》第1辑(文物出版社1997年)。
[47]照那斯图:《八思巴字篆体字母研究》,《中国语文》1980年第4期。
[48]照那斯图:《八思巴字与蒙古语文献I研究文集》,东京外国语大学语言文化研究所发行1990年。
[49]照那斯图:《台湾故宫藏几方元八思巴字印译释》,《民族语文》1997年第10期。
[50]叶其峰:《故宫藏元八思巴字印及相关问题》,《文物》1987年第10期。
[51]杨永财:《八思巴文“元押”印章在杜尔伯特出土》,《黑龙江民族丛刊》2014年第4期。
[52]《风从北方来—内蒙古八思巴文篆刻进京展元代八思巴文印章选》,《中国书法》2018年第8期。
[53]哈斯喜贵:《哈斯喜贵篆刻集》,西冷印社出版社2018年版。
[54]刘玉江:《哈斯喜贵篆刻艺术》,《中国书法》2019年第7期。
{55]于佳音:《回鹘文经济文书t(a)mya和ni(?)an研究》,中央民族大学2015届硕士学位论文。
[56]照那斯图:《蒙古字韵校本》,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
[57]孙家潭:《关于八思巴文字印释读的几点体会》,《中国书法》2018年第8期。
[58]赵芯:《姓氏押之汉字“姓”和“花字”押》,《东方教育》2018年第21期。
[59]法国,龙乐恒:《伯希和旧藏花押印集》,西冷印社。
[60]伯希和:《八思巴文字母渊源考》演讲,尚未发表,总结见《亚洲学报》1927年4至6月,第210卷,第372页。
[61]伯希和:《发现于河西的白鸽、十字刑铜质印符考》,《亚洲艺术杂志—吉美博物馆年鉴》1931—1932年,第七卷,第1—3页。
[62]日,石黑ひさ子:《墨书陶瓷上的花押和宋元花押印》,收录于《第五届孤山证印西冷印社国际印学峰会论文集》,西冷印社出版社2017年版。
[63]日,久米雅雄:《日本花押与中国大名印章》,收录于《西冷印社国际印学研讨会论文集世界图文与印记》,西冷印社出版社2018年版。
元押之图像印的探究
2020级美术学 汤松菡
中国古代印文化,从先秦时期到秦汉、魏晋南北朝再到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印材上以铜印和石印为主,玉印相较为少数,而用象牙、竹子、花乳石等制印的更为少有,制造方式上以铸造、刀刻为主,在风格特色、形制等方面,则更加的多样,随着时代的更迭发展,印文化也在不断的吸收革新。其中,花押的发展在元代进入了更为普遍和突破性的创新阶段,花押早在宋代以前就已经出现,历史悠久,韦陟“五朵云”就是重要例证,据明代陶宗仪所说,花押入印始于五代后周,发展至宋代,花押被广泛运用,不再局限于某一阶级,上至天子诸侯,下至黎民百姓,至于元代,花押的发展更为繁盛,现如今传世的花押印多为元代所制,宋代花押印并不多见,故又将花押称为元押或元戳。
元代时期,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多民族文化碰撞交融,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促使了花押印在飞速变化发展的社会生活、艺术创作中产生更加适应时代要求的变化,变化发展的印章顺应了市场需求,民间私印大量涌现,官方押印也有可观的发展。押印在这一时期顺通南北东西,亦是汉族与少数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产物。元押印的印形除了常规的长方形、圆形等,还有以动物、人物、琴类、植物、器物等为外边界的印式,如兔、鱼、马、鸡、琵琶、葫芦、香炉等。用途方面,元押印可用于机构办公、私人签署、商贸、宗教传播等,商贸文件签署是其主要用途,元押印均为传世品,无葬印的发现。元押印大都为楷书入印,少有篆隶入印,印风延续魏晋碑刻一脉,但风格多样,有古朴厚重之风,也有飘逸秀美之感。按照内容和形式来区分,大致可分为五大类。第一类:楷书汉字与花押的结合,此类传世时间最长,也是元押印现存数量最多、种类最为丰富的一类,按照印形与楷书花押排列方式的不同又可细分为两类,长方形印面上部为楷书汉字,下部花押,方形印有上为楷书汉字下为花押,亦有左右汉字,中间花押,楷书汉字与花押交相辉映、动静相随、浑然一体,是元押印的一大风格特色。第二类:只有楷书汉字,无花押。例如常见的姓氏印,印面上单有一个姓氏,如“刘”。第三类:只有花押,无楷书汉字。又可细分为全框花押、半框花押、无框花押,有框花押外形常为方形和圆形,半框花押上下封住,左右开口,上部多为一细横,下部为一粗横,无框花押则随意开放,形态各异,装饰性极强。第四类:异族文字押印,这里的异族文字指的是汉字印以外的少数民族文字印,如八思巴文印、西夏文印、契丹文印等。第五类:图像印。
人物形押“大吉” 葫芦形押“大吉”
葫芦形押“大吉” 瓶形押“大吉”
瓶形押“大吉” 鼎形押“大吉”
鼎形押“大吉”
“王记”鱼形押 鹿形押“福”
鹿形押“福”  人物形押
人物形押 琵琶形押
琵琶形押 
锭形押  人物形押“大吉”
人物形押“大吉”
元花押印之所以有别开生面的开创性局面,主要有三方面,第一是因为楷书大量入印,打破了传统的已趋于古板呆滞的篆书入印的规制,第二则是多种少数民族文字的入印,无论是汉字与少数民族文字结合入印,还是纯少数民族文字入印,奇幻莫测的多文化的结合都给元花押印增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第三则是样式多样的图像印,按内容可分为人物形押、动物形押、植物形押;器物形押等。
在史料记载中,图像印自战国到汉魏皆有,以汉代为一高峰,元代时期是图像印发展史上的又一高峰,探究元图像印盛行的原因,以它从属的大类及元押为基点,翻阅相关资料后,笔者发现大部分学者认为是因为蒙古人入主中原后,在国内划分了四个民族等级,地位最高的是一等蒙古人和二等色目人,但他们大多不识汉字,不能执笔画押,所以简单易懂的花押印便顺势而起,而图像印作为一种比文字更为直观、明了的印迹,在吸收了民间以及前代的种种风气后,以一种别样的姿态重现出现在我们面前。然而在周晓陆先生所著的《元押》中,出现了对花押印在元代盛行的原因的不一样的见解:“《辍耕录》中,时时洋溢着对异族的忿懑之气,所以我看这段文字,不免有揶揄之意。而今一些研究者则坚信陶夫子之言凿凿,又加上元代文献对押印戳记没有更丰富详实的记载,所以造成坚信不疑者有的更近一程传讹,说是元代的官几乎都是些文盲,所以除文书无法读通外,好像连公私印章凭信上的几个字也不能认得,所以只能仰赖押印戳记上的朵朵花儿了。我以为陶夫子之说已与实际情况有所偏差,就元代的吏制管理情况来看,还没有大量文盲充斥官场的情况。”[1]笔者认为,无论这两种见解哪一种更与现实相符合,元代的蒙古人和色目人对元押的传播和创新都是不可质疑的,元图像印也是元人在学习和探索汉族文明的过程中自我审美更新的产物,对元风的形成也有重要作用。
元代图像印承古开今,在承古方面,陈宇在他的《元代押印》中有言:“元代图像印不但继承了秦汉图像印、石刻画像的旨趣以及汉代瓦当艺术中强调物象的艺术特点,最根本还在于,它化合了中国绘画艺术中的写意画风和书法艺术中的笔墨技巧。”[2]秦汉图像印、石刻画像古拙质朴又妙趣横生的意趣,汉代瓦当艺术中强调物像的创作规则,中国山水画中的写意之法以及书法中的笔墨之法,元代图像印方寸之间的墨法百态,清丽飘逸又不失强劲有力,古朴浑厚但又趣味十足,虽是承袭前代之风,但元代图像印并没有完全照搬前代风格,从艺术的再生性和开创性来讲,元图像印与秦汉图像印相比,更富有变化和张力,元代图像印集书法、篆刻、绘画等为一体,既是多样艺术的综合体现,也是元人敢于尝试创新的与时俱进的宝物。元图像印的开今:元代社会的特殊性决定了元图像印不同于传统图像印的“异样”发展,社会组成成分改变,少数民族称为中原的掌控者,领导下的少数民族人民在融入中原汉族文化的过程中自身的需求也在不断地增加,两种文明的相互碰撞和融合,在更先进的文明中寻求解决自身问题的方法,相比于篆书与楷书汉字,图像印更能满足少数民族表达自身的要求,在创造自身文字和学习汉字的同时,图像的传达作用也必不可少。
在图像印所取用的元素方面,元图像印与秦汉时期的图像印又有着很大的不同。图像印的取材相当广泛,但根据朝代的变换、时代的变迁,所取用的题材也会发生明显的改变。图形印在过去有着“螭”纹、“生肖印”、“肖形印”等不同名称,但事实上,图像印的取材远不止“螭”、“生肖”,人物、车骑、禽兽、鱼虫等都可为其选取的对象。汉代图像印的选材不限于四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金乌、车马出行、人物杂耍、家禽、生肖等,神仙题材占多数,这与汉代厚葬之风的盛行密不可分,这一点也可以从汉代的画像石上得到认证,图像印算是画像石的平面复刻印,双方相互印证下更能证明结论的真实性。汉代图像印主要描绘的是天上的神仙世界,而元代图像印则又回归到了日常的生活中。元押中的图像印与传统民间吉祥图案有着共同的源流,如鹿代表着俸禄,龟代表着长寿,银锭代表着安定富贵,羊代表着吉祥,鱼代表着丰收有余等,这些都与百姓祈求的美好祝福有关,是百姓生活的反映,与汉代厚葬之风相比,元代似乎更注重现世的平安喜乐。元代在往常基本的长方形或圆形外框以外,又以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事物外形为轮廓,开拓出以各种物形为外边界的印式,如官服人物形、鼎形、香炉形、瓶形、葫芦形、莲花形、琵琶形、锭形、鱼形等,生动活泼、各具特色,为中国印界注入了一股清流,这些印式涉及生活中的吃、穿、用、行,浓缩了元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将元代社会面貌等比缩小,集于微小的印章之中,透过他们,百年前繁华的元朝之景穿过历史的尘埃稍加显露出一角,对后代研究元朝历史具有重要意义。元图形印也常常与文字相结合,将文字置于图形中间,以图形本身借喻文字,比如“平(瓶)安”等。兔、鸡、牛、羊等家畜家禽也是元图像印中常见的元素(图1、图2)[3],莲花形图像印章、花瓣形图像印章(五瓣、八瓣等)也较为常见(图3—6)[4]。通过对比各个朝代图像印的内容,可以发现,元代图像印中家禽的元素大大增多,这可能与少数民族的游牧文明以及对汉族文明的尊崇有关。


图1 图2




图3 图4 图5 图6
总之,元图像印继往开来,在承接秦汉文明的同时,也为元代文明增添了光彩。元帝国兼容并蓄、包容开放,在多民族、多文化、多宗教的宏大背景下,元图像印生机勃发,元人意趣盎然、天真璀璨的审美情趣和创作观念尽在不言中。
注释
[1]周晓陆:《元押》,江苏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
[2] 陈宇:《元代押印》,《江苏教育-书法教育》2016年第9期。
[3] 图一:榆林朔方博物馆藏,图二:陈宇《元代押印》。
[4] 榆林朔方博物馆藏